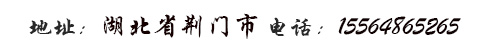白芥子与莱菔子临床应用类辨附伤寒论第
|
白芥子与莱菔子临床应用类辨 白芥子味辛,性温。能入肺散寒,利气豁痰,散痛消肿。对寒痰壅滞引起的胸满胁痛,咳嗽气逆,痰多等症有良好的疗效。本品善于温通经络,能透达经络凝聚的寒痰,所以又可用于痰核、阴疽、寒湿引起的骨痛等症。 用白芥子为末,醋调涂肿毒初起有效。 莱菔子味辛、甘,性平。它的主要作用为消导食积与祛痰降气。由于它既能化痰又能消食,所以对痰食互滞之症,功效尤其显著。 通过临床实践,本品适用于久咳痰喘实症,如属肺肾虚咳喘满者,效果不好。 本品炒用能降气祛痰,生用则涌吐痰涎。 ?《伤寒论》第三十七条小柴胡汤各家解说 《伤寒论》条文: 太阳病,十日以去,脉浮细而嗜卧者,外已解也。设胸满胁痛者,与小柴胡汤。脉但浮者,与麻黄汤。 ?《刘渡舟伤寒论讲稿》 这一条论述太阳伤寒日久的几种转归。 这里的“太阳病”,从后文“脉但浮者,与麻黄汤”,可知指的是太阳伤寒。太阳伤寒已过十日,脉由浮紧变为“浮细”,也就是说脉虽浮,但不那么紧急有力,同时仅见乏力而“嗜卧”,而恶寒发热、头项强痛之证已除。以上脉证说明,表邪已去,正气渐复,已无所苦,故谓“外已解也”。既然外邪已解,虽然觉得略有不适,也不需要服药,只要安心静养即可,是第一种转归。“脉但浮者,与麻黄汤”,是说太阳伤寒虽已过十日,但还见伤寒的浮紧之脉,并以此暗示太阳伤寒的恶寒发热,头身疼痛诸证仍在。既然脉证仍在,病仍在太阳,属伤寒表未解,故治法与方药也应该不变,仍应考虑使用麻黄汤。但由于“十日以去”,病程日久,即使伤寒诸证仍在,可以再用麻黄汤发汗,也应当谨慎使用,因此不说“主之”,而说“与”,这是有区别的。以上属于表邪留恋未解,是第二种转归。如果证见“胸满胁痛”,反映少阳枢机不利,说明邪气已由表传入少阳之经,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,以利枢机,是第三种转归。 从这一条所举太阳伤寒日久的几种转归可以看出,虽然“太阳病,十日以去”,但病邪却不一定会发生传变。其中有向愈者,亦有表邪仍不解者,只要表证不解,就应当再用解表的方法治疗。凭脉辨证是推断病情发展变化的主要依据,不可拘泥于病程长短,这个精神在这一条又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 ?曹颖甫《伤寒发微》 太阳病十日以去,则已经过七日之期,诊其脉,浮而细,则标阳已衰。嗜卧,则表热已退。由躁而静,其为太阳解后,不传阳明可知。若水气留于心下而见胸满,水气结于肾膀之上而见胁痛,则为太阳水气内陷。故同一浮细之脉,水气由少阳三焦牵涉寒水之脏腑,则外仍未解。寒水之藏,属足少阴,故脉细。此时虽无潮热,而太阳水气未尽,故仍宜小柴胡汤以解外。故脉但浮而不细者,水气当在膈上,而但见胸满之证,与上节麻汤证同,不定牵涉足少阴而并见胁痛,故不见少阴微细之脉,此当于无字处求之者也。 尤在泾《伤寒贯珠集》 太阳病,至十余日之久,脉浮不紧而细,人不躁烦而嗜卧,所谓紧去人安,其病为已解也。下二段,是就未解时说,谓脉浮细,不嗜卧而胸满胁痛者,邪已入少阳,为未解也,则当与小柴胡汤;若脉但浮而不细,不嗜卧者,邪犹在太阳而未解也,仍当与麻黄汤,非外已解,而犹和之发之之谓也。 汤本求真《皇汉医学》 当患太阳病,经过十日以上尚不愈时,呈脉浮细而好横卧者,表证之谓外,即表证已解也。设有此状,而胸满骨痛者,可与小柴胡汤。脉但现浮,无他证者,为表证未全去,宜与本方之意也。本条所以称与,不称宜者,称宜为应一时病变之活用手段而权其机宜也;称与者,见目前之证,为一时的处方之谓,寓有依证变化或至于转方,亦未可知之意也;至病证完备,无丝毫疑者,则称主之,是三者之区别也。 ?《胡希恕伤寒论讲座》 “十日已去”,这个“已”不是那个“以”,赵开美《伤寒论》本子上是错的。这一条我们在临床上最多见了。得感冒不一定得十日已去,据我个人观察,三四天就有这个事,表没有了,但脉还是浮,浮可是细。脉细就是津虚血少了,脉浮细就是在表的津液也虚了、血液也不足了,它是在表。这个人同时也嗜卧。嗜卧是半表半里尤其是少阳病的一个特殊症候,少阳篇里它都没提(嗜卧),尤其他是个柴胡证,一会儿我们可以慢慢地讲。这个(柴胡证)在临床上常见的,看到脉浮,你再给吃发汗药就不对了,这是“外已解”呀。因为什么?脉浮细。病人假设同时又发生“胸满胁痛”,胸满胁痛是柴胡证,胸也满,两胁也疼,我们讲到柴胡汤你们就明白了。柴胡汤里说是里了,人就是困倦无力而嗜卧。 “血弱气尽,腠理开”。病开始在表,那么患病的机体打算发汗,所以把体液都输送到体表来了。你看我们讲桂枝汤讲麻黄汤都是这样子,就打算出汗。可是这个阶段(欲出汗)过去了,疾病在表(的正气)支持不了了,它还(要)与疾病不断斗争,但是不能在表了,就打算在半表半里。半表半里就是借助肺、肾脏等,就是各种脏器协和的力量,由呼吸道、泌尿系,或者是再由汗腺等各方面排出这个病。(但)这时候表面上血弱气尽,我们讲柴胡汤就有了,血也弱,气也尽,它都撤出(表)这个防线,加强里头防线,要是以打仗为比喻的话。在表津液血液都少,所以就在这个时间“脉浮细而嗜卧”。我们在柴胡汤证里头讲“血弱气尽,腠理开,邪气因人”,邪往里头走,就在胸胁的部位,结于胁下,所以咱们一得少阳病,就胸胁苦满嘛,正邪在这个地方纷争。 这段就说的这个:本来在太阳病的时候脉不细,脉虽浮但不细。脉一见细了,虽浮,在体表的津液血液都不足了,病就有入内之势,如果人再嗜卧,波及内脏人就困倦了,“外已解”,这是外头的表证完全解除了。那么这时候看是不是柴胡证,光一个嗜卧还是不行的,如果再胸满胁痛,柴胡证才算是具备了,那就“与小柴胡汤”。 他这个书又怕你误于这一点,说十几天了就这样子(由太阳病变少阳病),这不一定。说“脉但浮者,与麻黄汤”,十几天也好,再日久也好,脉但浮,不细,而且也没有这一系列的症候、外证,就是嗜卧、胸胁满等都没有,那你该解表还得解表,没有汗,还是用麻黄汤,这后头也有。所以在临床上,不能有主观,说十几天表证应该没有了吧,(但可能)就有嘛,就有你还得解表。前边这种情形(由太阳病变少阳病)很普通,十几天表不解的(仍为太阳病)也有啊,他怕你固执于“十日已去”。 那么如果“脉浮细而嗜卧”,这肯定是病传变了,病都是由表传半表半里,再传里,或者由表传里,仲景这个书是这样的,与《内经》上不一样。《内经》说一日太阳,二日阳明,三日又跑到少阳去了,(仲景)他这个书不是的,你们看就能看出来了。在临床上我们常遇到,这个人高烧不退,可是摸着脉有点细,虽浮而细,这个人困倦无力,这个时候差不多这些病都要来了:恶心,胸胁满,也有时候往来寒热,这都是柴胡证。这个时候用柴胡汤为主,没错的。如果口舌干燥,舌再有白苔,你还要加石膏,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是常见着,所以这一段书挺重要,因为这是我们最常遭遇的事情。大概我刚到(北京中医)学院的时候,大家还都不敢用柴胡呢。那阵儿都说柴胡升散,都怕用它,近几年好了,现在一般人都没有这想法了。所以在临床上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,有一般的这种高烧,多少日子不退,他不知道用柴胡汤,可是这个病始终不好。(其实)全是这个问题,就是“十日已去,脉浮细而嗜卧”,这类的情况遭遇的最多。 小柴胡汤,主要以柴胡为主药了,你看看它用的量是半斤,这古人半斤,就是一剂分三付的话,每一付还得八钱呢。黄芩与柴胡这两个药,全是苦寒药,解热去烦。柴胡这个药在《本经》上说得很清楚,它就是“主心腹肠胃间结气”。结气,就是结于胁下这个结,所以它治胸胁苦满,从胸到心下就是胃到腹,胃肠中结气邪气。推陈致新,它就是这个作用。所以柴胡配合黃芩,既能解热,又能够去胸胁满和痛。 那么底下呢,用些健胃药,人参、甘草、大枣、生姜,都是健胃的,搁上半夏止呕,因为柴胡证是少阳病必呕啊,这个书这一节还没提,但是常呕、恶心。为什么搁这些健胃药啊?就是我们方才所说脉浮细,津虚血少了。津液虚、血少,血也是液,“血”不是咱们现在都知道的血球,不是血球少了,而是血液、血里面的液体少。津液少,血里的液体也少。那么津液的生成由哪来的呢?由胃来的。 咱们讲桂枝汤的时候讲了,外邪之所以进里,就因为津液在外边不足以驱邪了,所以邪才往里头走。那么这个时候,还得想法来对付疾病:趁着没入里,健胃生津。所以早先徐灵胎他说“小柴胡汤妙在人参”,就在这一点。可是如果这病已经进里了,这人参要不得,就不能够再健胃了。病已经进里边了,你把门关上了,那就是关着门抓贼嘛,那还行吗? 它(病邪)没进来(入里),外边的气血已经虚了,(需要)健胃,就是补中益气这种意思,所以在小柴胡汤里头,特别用健胃有力的人参。另外呢?有半夏配伍生姜,它止呕的,这个后头讲柴胡证的时候咱们再详细讲,这里略略地提一提。 所以(小柴胡汤)这个方剂,它既是个解热剂,同时也是个健胃剂,健胃止呕。那么小柴胡汤证大概都是胃不好,这我们在临床上也常见,(否则)为什么他呕呢?所以(仲景)他这个书也是,不呕就是没有少阳病,不渴(就是)没有阳明病,阳明病准渴,少阳病准呕,后头再详细讲,这个咱们先撂到这块。 成不居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laifuzia.com/lfzzy/1782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民间散佚中医名方七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